我们枕着花香入睡,浮游在花香里饮食起居,世事悠然,无哀无忧。

喜欢一些开白花的灌木类花树,像茉莉、木槿、栀子……开起花来,一朵朵都是心思简静,悠然芬芳。
在南方,在乡下,一个女孩子,几乎都有一棵栀子花树伴她长大。五六月的初夏天气,乡村沉陷在疯长的绿色里,一朵朵淡雅的栀子花便开始打扮乡村了。女孩子的日月过得都有仙气,开门见花,闭户则花香缭绕。依花长大的女孩,长得也像栀子花一样素洁婉丽。
童年时,我家有一棵单瓣栀子,大伯家是一棵重瓣栀子,都是姑姑在出嫁前栽的。花树大了,开花了,我和堂姐刚好到了戴花的年龄。
那时候,还没起床,母亲已经将带露盛开的栀子花掐回来,就等我起床梳辫子戴花。我坐在窗台边的椅子上,闻着花香,觉得晨晓潮凉的空气都有殷勤待我的情意。戴着洁白的栀子花,穿上杏黄色的连衣裙,背着小书包,走在乡村的小路上,我觉得整个世界都好美。自己像是一只白色的蝴蝶,幻作了人形,来人间游览,处处都有新奇和感动。多少年过去,我一直觉得那一段时光最有人间的美意。
少年时读过一首古诗:“雨里鸡鸣一两家,竹溪村路板桥斜。妇姑相唤浴蚕去,闲看中庭栀子花。”读过就喜欢得要命。成家后,住公寓楼,养花不易。幸运的是住一楼的邻居家有个庭院,院子里栽有栀子花。我就有福气了,时常傍在阳台边,享受那摇荡蓬勃的花香,领受着饱满甜蜜的情意。后来,又贪心,终于抱回一大盆栀子花,养在家里,一养多年。养花养到后来,就像养了一个女儿,一边欢喜,一边念念放不下。花开时节,一朵一朵的白蝴蝶落在绿叶里,或藏或现,或豪放或婉约地开。我们枕着花香入睡,浮游在花香里饮食起居,世事悠然,无哀无忧。
有一年,在北京的一处广场边,看到有人卖花,其中就有栀子花。那花枝叶稀疏,花开胆怯,眉目之间甚是楚楚可怜。可能还是气候和水土的原因,养得不够丰润有神采。我彼时离家已有些日子,再见栀子花,如遇流落在此的故人,又感动又心酸。身边是一位西北长大的朋友,我问她,知道那是什么花吗?她一脸懵懂茫然。她说她们那边没有栀子花,也没有莲藕,没有芦苇,没有菱角……我听了,替她遗憾半天。我一直以为,有家的地方,就有栀子花,有村庄的地方就有栀子花。人总要在水气和花气里长大。
在苏州,在南京,在长江中下游一带的江南江北,初夏路过人家的院子前,一路是栀子花的香气相迎相送,让人觉得,这尘世美好得每一分每一秒里都充盈着爱意。
我奶奶青年时守寡,她自觉是个不幸的人,自此穿衣再不穿艳色,连从前的绣花鞋子也摁进了箱底。但是,却一辈子保持着戴栀子花的习惯。初夏的浓荫下,坐着一位身穿藏青色斜襟褂子的老人,她的头发绕在脑后,挽成一个扁圆的髻,髻边斜插一朵栀子花。她颤颤走动在树荫下,一阵一阵的花香软软袭来。戴花的奶奶,便有了观音一样慈悲温和的美。
栀子花,开在南方多雨的庭院里,开在简洁庸常的平民生活里。它多像一个素色的女子,没有遗世独立,也不轻易伤感。她只以一种温婉清美的姿态,将一种小格局的生活撑得格外饱满,别具情味。
选自《散文》2015年8月
赏析:

第一次听说栀子花,是在唐代诗人王建的《雨过山村》里——“雨里鸡鸣一两家,竹溪村路板桥斜。妇姑相唤浴蚕去,闲看中庭栀子花。”作者本是写江南乡村人家闲适生活的,却把庭院里盛开的白色栀子花灼灼开放在每一位读者的心里,尤其是对于来自北方、不曾见过栀子花的人来说,更是对栀子花充满了向往之情。在作者的娓娓讲述中,我们才知道,在南方的乡下,每一个女孩子,几乎都有一棵栀子花树伴她长大,清晨开门见花,闭户则花香缭绕,而依花长大的江南女孩,长得也像栀子花一样素洁婉丽——所说的花样女孩,即是如此吧。栀子花,就这样充溢在江南乡下女孩的琐碎生活中:清晨,还没起床,母亲已经将带露盛开的栀子花掐回来,准备给女孩梳辫子戴花; 女孩起床后,闻着花香,觉得晨晓潮凉的空气都有殷勤的情意;去上学时,女孩戴着洁白的栀子花,穿上杏黄色的连衣裙,背着小书包,走在乡村的小路上,觉得自己像是一只白色的蝴蝶,整个世界都那么美好……
栀子花带给作者如此美好的回忆,以至在她成年之后也痴迷于养花,“就像养了一个女儿,一边欢喜,一边念念放不下”。在作者的心目中,栀子花,是属于家、属于水乡的,因为人总要在水气和花气里长大;栀子花,又是属于女孩的,它是那般温婉美好,代表了女孩子对生活的希冀与向往。其实,栀子花的平易简单、素色娴静,也像极了我们所追求的一种生活格调——简单、纯粹、温婉、宁静。
来源:语文报初中版
注:本文部分文字与图片资源来自于网络,转载此文是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,若有来源标注错误或侵犯了您的合法权益,请立即后台留言通知我们,情况属实,我们会第一时间予以删除,并同时向您表示歉意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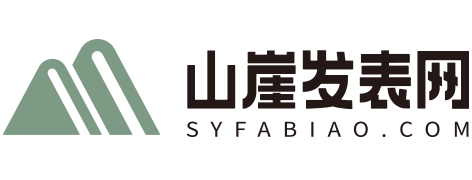
发表评论